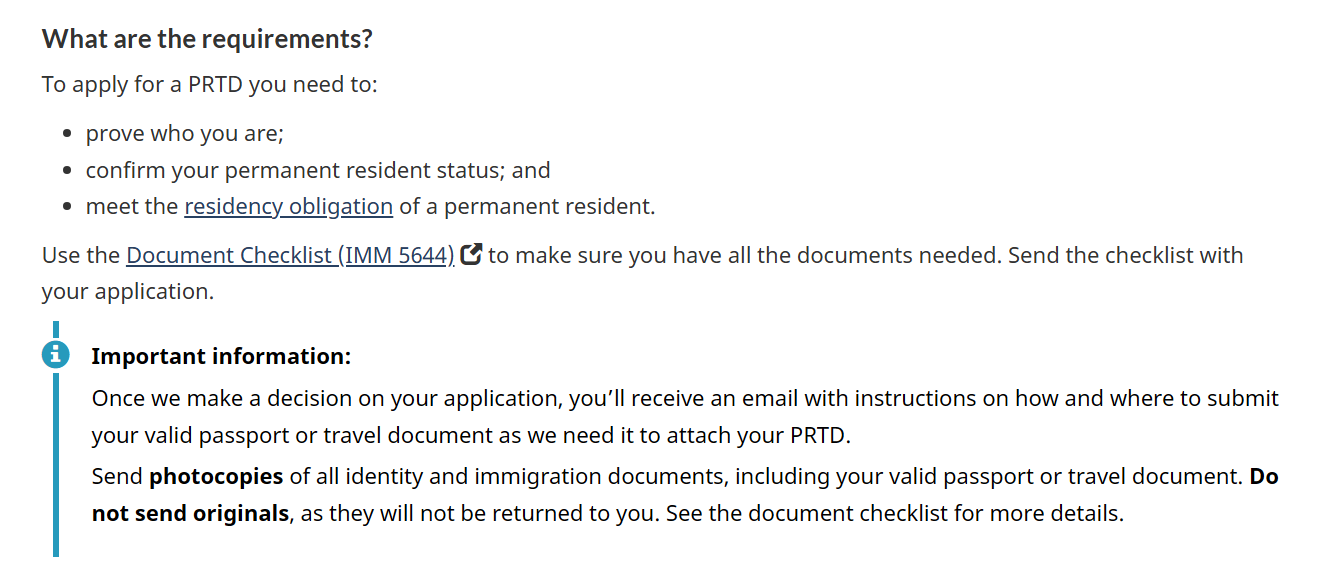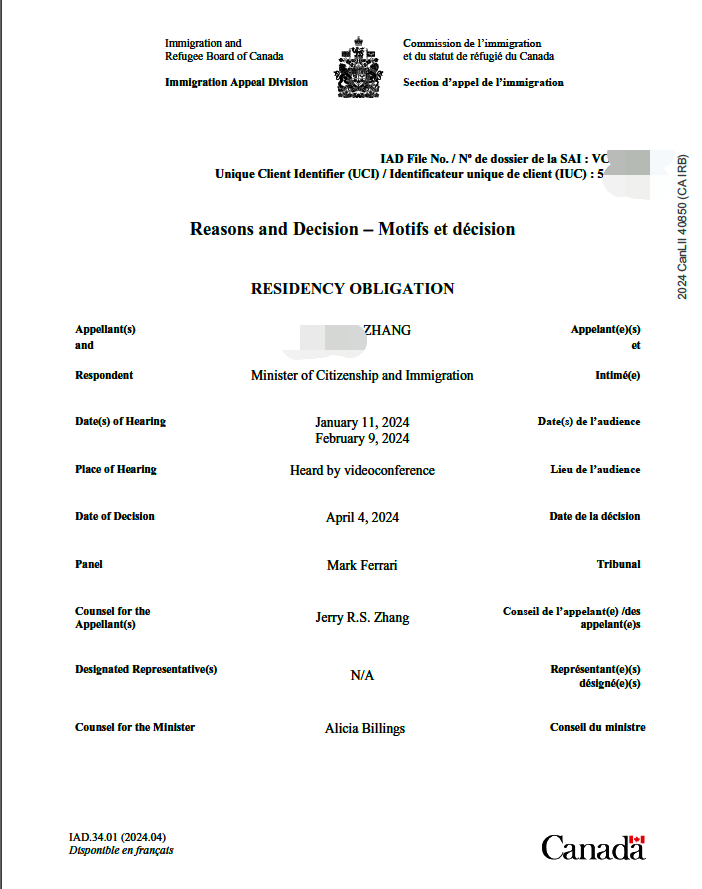拍案惊奇:华裔老妇申请加拿大PR旅行证被拒 高法复议也被驳回
未满足居住义务可能会导致移民身份被取消或者被拒绝续签。在许多国家,移民身份通常会有一些义务和条件,包括居住要求。如果一个人未能履行这些义务,比如没有居住在指定的地区或者没有满足规定的居住时间,移民局可能会采取行动,例如取消其居留权或者拒绝其续签申请。
司法复核
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72条,您可以在获得联邦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向该法院申请对移民部门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核。您可能希望尽快获得律师的建议,因为该申请有时间限制。
一位2014年起居住加拿大的中国籍八旬老妇,2019年回中国之后再没踏足加拿大,当她在2022年申请永久居民旅行证件时(PRTD),被加拿大移民部拒绝,理由是老人未有履行在加拿大居住的义务。
老人以“人道主义和同情”及疫情时没法回来的理由向移民上诉庭上诉,但还是被驳回。
文件显示,这位在2014年抵达加国投靠女儿的81岁张老太(Zhang,音译),在相应的5年期限内,在加拿大仅居住了538天,没有达到《移民法》规定的最少730天的最低要求。
对此张老太辩解称,她在2019年11月回到中国探望儿子,还想顺便与朋友们一道去日本旅行,并在那里乘坐邮轮。
但不久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她无法返回加拿大。到2022年国际旅行限制取消后,她也曾想过返回加拿大,但考虑旅途的安全,于是作罢。
对于这一点,上诉庭法官法拉利(Mark Ferrari)认为张老太的证词可信度低且缺乏说服力,回答问题时还往往相互矛盾或缺乏连贯性,降低了法官对证词的重视程度。
法官举例称,张老太认为疫情令旅途不安全,不敢乘坐航班返回加拿大,却敢在2019年12月26日前往日本坐邮轮。
另一个例子是,张老太称自己不敢独自飞回加拿大,但事实是,张老太从加拿大回中国时就是独自一人。张老太进一步辩解称,她回中国是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但这家公司却没有飞返加拿大的航班。
《移民法》规定永久居民在5年期限内,至少在加国居住730天的要求。
关于中国的航空公司何时停飞加拿大航班,张老太提供的证据很少,也没有试图联系过其他的非中国航空公司,看他们是否有航班。虽然可以理解张老太更愿意搭乘中国航班,但她没有试图联系其他航空公司看是否有中文服务,就完全放弃了回加拿大的打算,这难以解释。
张老太还表示,她无法在中国接种加拿大政府认可的疫苗,使她无法回加拿大。法官指出,张老太及其家人从未在国外或国内与加拿大政府联系查询求助。而签证处的说明显示,自2020年3月起,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返回加拿大已经基本不受限制。
此外,张老太在加拿大既没有工作也没有资产,虽然有加入当地教会,经常参加教会活动并担任志愿者,女儿、女婿和4个外孙也住在加拿大,但从张老太长时间离开加拿大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来看,女儿一家对张老太的依赖性并不强。
张老太的4个外孙,有两个已经成年,年幼的也有十多岁,全部都成功实现学业和职业目标,不受张老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影响,相反张老太连外孙的学业情况甚至年龄都回答不上来。
张老太的辩护人声称,在中国文化中孙辈的年龄和学业情况并不重要。法官对此说法“不予重视”。
而且法官还认为,尽管相隔遥远,但张老太与女儿一家多年来一直能够保持沟通,此种情况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就算想亲身探望,办理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或超级签证也不是什么难事。
相反张老太在定居加国之前,长期居住在中国。如今她住在女儿移民后留下的中国房产内,还有她儿子的关照,生活很美满。
法拉利法官最后裁定,张老太没有履行举证责任,证明她失去永久居民身分会对儿孙的最佳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也就缺乏足够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因素来支持对她的特别救济,由此驳回张老太的上诉。
参考翻译:未满足居住义务 加拿大移民身份被撤 申请司法复核 大法官驳回上诉
上诉人 张x芳
上诉人律师 Jerry R.S. Zhang
答辩人 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
代理律师 阿莉西亚-比林斯
听证日期 2024年1月11日 2024年2月9日
听证地点 通过网络视频
裁决日期 2024年4月4日
法庭法官 马克-法拉利
案情概述
[1]张x芳(上诉人)是一名81岁的中国公民,于2014年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2]自登陆以来,上诉人主要居住在加拿大。也曾多次返回中国探亲。2019年11月,上诉人回中国后,再未回过加拿大。
[3]2022年,上诉人申请永久居民旅行证件(PRTD),但被认定不符合《移民和难民保护法》(IRPA)第28条的居住义务要求。
[4]上诉人并未质疑关于她未履行居住义务要求的裁定的法律效力。但是,上诉人以人道同情为由向移民上诉庭IRB提出上诉。因此,本案的问题是,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67(1)(c)段,尽管上诉人违反了居住义务,但移民上诉庭IRB是否应行使权力酌情给予宽待,允许上诉人保留其永久居民身份。
[5]我认为上诉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根据我所掌握的证据,并权衡各种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受该决定直接影响的儿童的最佳利益,本案没有足够的人道同情考虑因素来支持特别宽待。因此,驳回上诉。
案情分析
上诉人、她的女儿和牧师在听证会上作证。我考虑了证词、案件中的材料、文件证据和双方的陈述。
适用法律和违规程度
[7]我认为关于上诉人不符合居住要求的裁定是合法有效的。
[8]《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28条规定了多种履行居住义务的方式。根据文件证据,上诉人在相关期间在加拿大居住了538天。
[9]上诉人没有质疑关于她不符合居住要求的决定的法律效力。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上诉人以任何其他方式达到了居住要求。
人道同情因素框架
[10]尽管上诉人违反了居住义务,但移民上诉庭有权考虑给予特别宽待和赦免,允许上诉人保留其永久居民身份。在行使这一权力时, 鉴于案件的所有情况,有足够的人道同情考虑因素证明有必要给予特别宽待:
- a)上诉人未履行居住义务的程度;
- b)上诉人离开加拿大的原因和长期留在境外的原因;
- c)上诉人是否曾努力争取第一时间返回加拿大;
- d)上诉人是否在加拿大建立了生活和工作的牢固根基;
- e)上诉人与加拿大的家庭关系;
- f)如果上诉人失去在加拿大的身份,将给其在加拿大的家人造成的困难和扰乱;
- g)驳回上诉是否会给上诉人造成的困难; 及
- h)驳回上诉是否直接影响在加拿大的儿童的最大利益。
[12]居住义务并不难实现。他们只要求在任何五年内居住730天,而且这些天数不必是连续的。在本案中,所需的730天居住时间严重不足。为使上诉获准,需要有与违反义务的严重程度和本案情况相称的人道同情因素。
离加原因和争取第一时间返回加拿大的努力
[13]在综合考虑证据时,我认为上诉人离开并长期留在加拿大境外的原因以及她为第一时间返回加拿大所做的努力对考虑给予特别宽容措施没有帮助。我对这些理由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14]上诉人作证说,她于2019年11月前往中国探望住在那里的儿子。她还想和朋友一起去日本旅行,并在那里乘坐游轮。当她在中国时,中国开始流行冠状病毒。上诉人作证说,由于由于疫情导致的限制,她无法返回加拿大,只能留在中国。她曾试图在2022年疫情限制解除后返回加拿大。
[15]有关这一点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上诉人对问题的回答往往相互矛盾或缺乏连贯性。我认为这引起了对证词可信度的担忧,从而降低了我对证词的重视程度。
[16]例如,上诉人作证说,当她听说疫情大流行时,她没有返回加拿大,因为她觉得旅行不安全。然而,根据证据,在她得知大流行病的消息并对旅行的安全性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她确实在2019年12月26日去了日本,然后乘坐游轮。对于上诉人为何愿意前往日本和乘坐游轮,却不愿意乘坐航班前往加拿大,没有合理的解释。有证据表明,上诉人担心在航班上感染的风险很高。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去日本旅行期间或在游轮上处于密闭空间的风险较小。
[17]另一个例子是,上诉人作证说,即使她能找到飞往加拿大的航班,她也不会一个人乘飞机旅行。尽管如此,上诉人确实独自一人从加拿大飞往中国。当被问及此事时,上诉人作证说,她搭乘的是一家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但该航空公司无法让她飞回加拿大。但是,关于中国的航空公司何时停止飞往加拿大的航班,提供的证据很少。根据证据,上诉人作证说,她没有试图与其他非中国航空公司联系,看他们是否有航班。虽然可以理解上诉人更愿意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但她没有试图联系其他可能提供航班的航空公司,以了解他们是否可以向她提供帮助,以克服旅行中的任何障碍,如语言障碍。
[18]上诉人还作证说,她不能返回加拿大,因为旅行的要求令人不适。她提到了一些要求,如在飞机上必须戴口罩,或在旅行前后进行PCR检测。虽然可能会造成不便,但记录显示,尚不清楚在飞机上戴口罩等要求如何成为返回加拿大的障碍。
[19]上诉人作证说,她在中国无法接种加拿大政府批准的疫苗,这将成为她回加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及其家人并没有试图与国外或国内的加拿大政府联系。签证处的说明显示,自2020年3月起,永久居民可以免除许多旅行限制要求。此外,说明中还指出可以乘坐飞往加拿大的航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没有联系加拿大政府,看看他们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或者至少提供这些信息。此外,也没有合理的解释说明上诉人或其家人为何没有花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并确定她在2022年之前返回加拿大的选择。
在加拿大的生活根基
[20]我认为上诉人在加拿大的工作单位在考虑特别宽待时帮助有限。总体而言,证据表明,尽管上诉人已成为永久居民多年,但她在加拿大几乎没有工作。
[21]上诉人在加拿大没有工作经验,在加拿大也没有资产。
[22]上诉人通过教会建立了社会和社区联系。她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协助他们开展一些志愿者活动。该教堂的牧师写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
与加拿大家的庭关联考虑
[23]我认为,上诉人在加拿大的家庭所面临的困难无助于在本上诉中考虑给予特别救济。
[24]上诉人的女儿、女婿和四个外孙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在听证时,他们都已成年,只有两个最小的外孙还是青少年。
[25] 在登陆加拿大之前,上诉人已经与加拿大的大多数家庭成员分开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决定到加拿大生活和定居时,上诉人在加拿大的家人选择了在地理上彼此分离的生活方式。从证据来看,他们能够茁壮成长。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学业和职业目标,并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和社区。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上诉人因决定在不同国家生活而面临任何困难。
[26]从证据来看,上诉人及其家人之间关系密切。他们支持上诉人保留其永久居民身份,并写信表示支持。8如果上诉人不能返回加拿大永久居住,很可能会造成情感压力。然而,在上诉结果导致实际分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预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情感压力会构成不当的困难。
[27]尽管相隔遥远,但上诉人及其家人多年来一直能够保持沟通,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此外,上诉人还可以探索访问签证或超级签证等选择,以确定这些签证是否会增加探视或同居的机会。
丢失身份可能给上诉人造成的困难
[28]总之,我认为,如果上诉被驳回,上诉人将继续留在中国,她不会面临不必要的困难。
[30]上诉人一直住在女儿在中国的家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安排不能继续下去。上诉人的儿子住在中国,与上诉人关系良好。上诉人的姐姐也住在中国,但她们并不常见面。
[31]在听证时,上诉人的儿子住在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因为他要照顾生病的岳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安排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此外,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上诉人不能住在离她儿子更近的地方,即使是暂时的,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岳父。
[32]如前所述,上诉人是在加拿大生活时加入教会的。在中国时,她可以通过网络参加教会聚会。她还可以参加一个日常学习小组。我承认,虚拟参与其教会可能无法提供与亲身参与相同程度的社会联系。虽然这一点已经考虑过,但这并不是给予特别救济的重要依据。
是否直接影响儿童的最佳利益
[33]上诉人的两个最年幼的孙子被认定为在本次上诉中需要考虑其最大利益的儿童。我认为,在考虑给予特别救济时,这一因素没有帮助。
[34]上诉人的孙子已经十几岁了,根据证词,他们与祖母的关系很好。虽然我对此没有异议,但我发现有时似乎夸大了这种关系的深度。上诉人无法回答有关孙辈年龄或就学情况的基本问题。按理说,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所陈述的那样深厚,上诉人应该知道这些信息。
[35]在案情呈堂陈述期间,上诉人的无酬代理人指出,上诉人无法回忆起孙辈的年龄或学校的年级与其文化背景相符,但这一论点没有得到支持。此外,这一论点是在呈文中提出的,部长律师没有机会就此进行交叉质证。
[36]虽然大多数儿童都会从祖父母的关爱和支持中获得一些好处,但在本上诉案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祖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对儿童的最大利益是必要的。尽管上诉人多年来一直没有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但他们一直能够茁壮成长。
[37]孙辈的父母决定在加拿大居住和养家,他们知道上诉人不会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虽然他们希望将来可以担保上诉人,但这一点无法保证,而且他们面临着永远无法获得担保的可能性。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子女父母的选择被推定为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
结论
[38]上诉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根据我所掌握的证据,并考虑到受该决定直接影响的儿童的最佳利益,鉴于本案的所有情况,没有足够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因素来证明有必要给予特别救济。驳回上诉。
(签名) 马克-法拉利
日期 2024年4月4日